译文及注释
创作背景
赏析
苏舜钦(1008—1048)北宋诗人,字子美,开封(今属河南)人,曾祖父由梓州铜山(今四川中江)迁至开封(今属河南)。曾任县令、大理评事、集贤殿校理,监进奏院等职。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,为守旧派所恨,御史中丞王拱辰让其属官劾奏苏舜钦,劾其在进奏院祭神时,用卖废纸之钱宴请宾客。罢职闲居苏州。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,但不久就病故了。他与梅尧臣齐名,人称“梅苏”。有《苏学士文集》诗文集有《苏舜钦集》16卷,《四部丛刊》影清康熙刊本。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苏舜钦集》。
猜您喜欢
泥金小简,白玉连环,牵情惹恨两三番。好光阴等闲,景阑珊绣帘风软杨花
散。泪阑干绿窗雨洒梨花绽,锦澜斑香闺春老杏花残,奈薄情未还。 走苏卿
聪明的志高,懵懂的愚浊。一船茶单换了个女妖娆,像章城佛了。老卜儿接
了鸦青钞,俊苏卿受了金花诰,俏双生披了绿罗袍,村冯魁老曹。
张子坚席上
云林隐居人未知,且把柴门闭。诗床竹雨凉,茶鼎松风细,游仙梦成莺唤起。
湖上
去年香梅花带雪,赛到孤山社。酒从村店赊,船问邻僧借,梅花又开忙去也。
春晚
平安信来刚半纸,几对鸳鸯字。花开望远行,玉减伤春事,东风草堂飞燕子。
云林隐居人未知,且把柴门闭。诗床竹雨凉,茶鼎松风细,游仙梦成莺唤起。
湖上
去年香梅花带雪,赛到孤山社。酒从村店赊,船问邻僧借,梅花又开忙去也。
春晚
平安信来刚半纸,几对鸳鸯字。花开望远行,玉减伤春事,东风草堂飞燕子。
并梅兄,双蝶子,烟缕衫轻。凤凰钗、缭绕香云。淡梳妆,□得恁,雪腻酥匀。揉春捻就,更是他、花与精神。
黛尖低,桃萼破,微笑轻颦。早做成、役梦劳魂。好风前,佳月下,莫忘行人。扁舟去也,没个事、多样离情。
黛尖低,桃萼破,微笑轻颦。早做成、役梦劳魂。好风前,佳月下,莫忘行人。扁舟去也,没个事、多样离情。
 苏舜钦
苏舜钦 白居易
白居易 李商隐
李商隐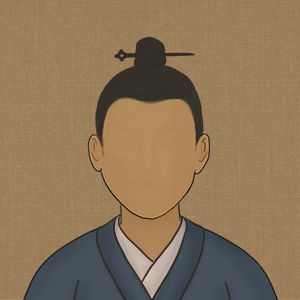 刘庭信
刘庭信 张可久
张可久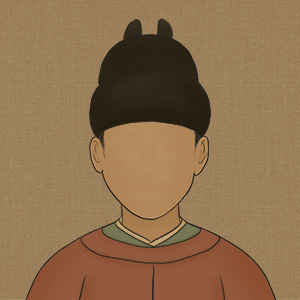 和凝
和凝 段克己
段克己 叶梦得
叶梦得 毛滂
毛滂 张元干
张元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