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作背景
赏析
王恽(yùn)(1227—1304年7月23日),字仲谋,号秋涧,卫州路汲县(今河南卫辉市)人。元朝著名学者、诗人兼政治家。一生仕宦,刚直不阿,清贫守职,好学善文,成为元世祖忽必烈、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铁穆耳三代著名谏臣。其书法遒婉,与东鲁王博文、渤海王旭齐名。著有《秋涧先生全集》。散曲创作,今存小令41首。大德八年六月二十日,在汲县去世,终年七十八岁。
猜您喜欢
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,最是不济事。
眼中了了,心下匆匆,方寸无多,往来应接不暇,如看场中美色,一眼即过,与我何与也?千古过目成诵,孰有如孔子者乎?读《易》至韦编三绝,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,微言精义,愈探愈出,愈研愈入,愈往而不知其所穷。虽生知安行之圣,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。东坡读书不用两遍,然其在翰林读《阿房宫赋》至四鼓,老吏苦之,坡洒然不倦。岂以一过即记,遂了其事乎!惟虞世南、张睢阳、张方平,平生书不再读,迄无佳文。
且过辄成诵,又有无所不诵之陋。即如《史记》百三十篇中,以《项羽本纪》为最,而《项羽本纪》中,又以巨鹿之战、鸿门之宴、垓下之会为最。反覆诵观,可欣可泣,在此数段耳。若一部《史记》,篇篇都读,字字都记,岂非没分晓的钝汉!更有小说家言,各种传奇恶曲,及打油诗词,亦复寓目不忘,如破烂厨柜,臭油坏酱悉贮其中,其龌龊亦耐不得。
杨柳深深小院,夕阳淡淡啼鹃,巷陌东风卖饧天。才社日停针线,又寒食戏
秋千,一春幽恨远。 春闺情
红日嫩风摇翠柳,绿窗深烟暖香篝,怪来朝雨妒风流。二分春色去,一半杏
花休,归期何太久?
秋千,一春幽恨远。 春闺情
红日嫩风摇翠柳,绿窗深烟暖香篝,怪来朝雨妒风流。二分春色去,一半杏
花休,归期何太久?
碧山锦树明秋霁。路转陡,疑无地。忽有人家临曲水,竹篱茅舍,酒旗沙岸,一簇成村市。
凄凉只恐乡心起。凤楼远、回头谩凝睇。何处今宵孤馆里,一声征雁,半窗残月,总是离人泪。
凄凉只恐乡心起。凤楼远、回头谩凝睇。何处今宵孤馆里,一声征雁,半窗残月,总是离人泪。
 王恽
王恽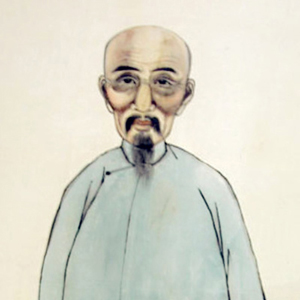 郑燮
郑燮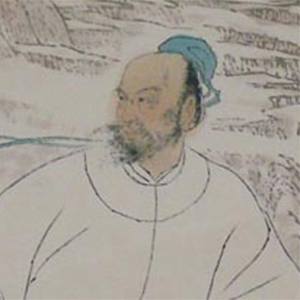 张养浩
张养浩 李致远
李致远 曹组
曹组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苏轼
苏轼 关注
关注 陈允平
陈允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