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创作背景
赏析
曹叡(204年-239年1月22日),即魏明帝,字元仲,豫州沛国谯县(今安徽省亳州市)人。三国时期曹魏第二任皇帝(226年至239年在位)。魏文帝曹丕长子,母为文昭甄皇后。曹叡能诗文,与曹操、曹丕并称魏氏“三祖”,原有集,已散佚,后人辑有其散文二卷、乐府诗十余首。
猜您喜欢
隋舰临淮甸,唐旗出井陉。断鳌支四柱,卓马济三灵。
祖业隆盘古,孙谋复大庭。从来师俊杰,可以焕丹青。
旧族开东岳,雄图奋北溟。邪同獬廌触,乐伴凤凰听。
酣战仍挥日,降妖亦斗霆。将军功不伐,叔舅德惟馨。
鸡塞谁生事,狼烟不暂停。拟填沧海鸟,敢竞太阳萤。
内草才传诏,前茅已勒铭。那劳出师表,尽入大荒经。
德水萦长带,阴山绕画屏。秖忧非綮肯,未觉有膻腥。
保佐资冲漠,扶持在杳冥。乃心防暗室,华发称明廷。
按甲神初静,挥戈思欲醒。羲之当妙选,孝若近归宁。
月色来侵幌,诗成有转棂。罗含黄菊宅,柳恽白蘋汀。
神物龟酬孔,仙才鹤姓丁。西山童子药,南极老人星。
自顷徒窥管,于今愧挈瓶。何由叨末席,还得叩玄扃。
庄叟虚悲雁,终童漫识艇。幕中虽策画,剑外且伶俜。
俣俣行忘止,鳏鳏卧不瞑。身应瘠于鲁,泪欲溢为荣。
禹贡思金鼎,尧图忆土铏。公乎来入相,王欲驾云亭。
月挂霜林寒欲坠。正门外、催人起。奈离别如今真个是。欲住也、留无计。欲去也、来无计。
马上离魂衣上泪。各自个、供憔悴。问江路梅花开也未?春到也、须频寄。人到也、须频寄。
马上离魂衣上泪。各自个、供憔悴。问江路梅花开也未?春到也、须频寄。人到也、须频寄。
余去岁在东武,作《水调歌头》以寄子由。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,过中秋而去,作此曲以别。余以其语过悲,乃为和之,其意以不早退为戒,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
安石在东海,从事鬓惊秋。中年亲友难别,丝竹缓离愁。一旦功成名遂,准拟东还海道,扶病入西州。雅志困轩冕,遗恨寄沧洲。
岁云暮,须早计,要褐裘。故乡归去千里,佳处辄迟留。我醉歌时君和,醉倒须君扶我,惟酒可忘忧。一任刘玄德,相对卧高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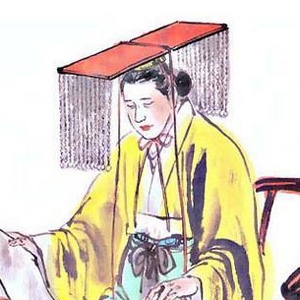 曹叡
曹叡 白居易
白居易 李商隐
李商隐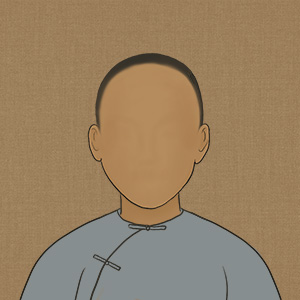 王国维
王国维 程垓
程垓 李清照
李清照 苏轼
苏轼 李白
李白 陈允平
陈允平 石孝友
石孝友 毛滂
毛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