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谏
太宗威容俨肃,百僚进见者,皆失其举措。太宗知其若此,每见人奏事,必假颜色,冀闻谏诤,知政教得失。贞观初,尝谓公卿曰:“人欲自照,必须明镜;主欲知过,必藉忠臣。主若自贤,臣不匡正,欲不危败,岂可得乎?故君失其国,臣亦不能独全其家。至于隋炀帝暴虐,臣下钳口,卒令不闻其过,遂至灭亡,虞世基等,寻亦诛死。前事不远,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,必须极言规谏。”
贞观元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正主任邪臣,不能致理;正臣事邪主,亦不能致理。惟君臣相遇,有同鱼水,则海内可安。朕虽不明,幸诸公数相匡救,冀凭直言鲠议,致天下太平。”谏议大夫王珪对曰:“臣闻,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。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,言而不用,则相继以死。陛下开圣虑,纳刍荛,愚臣处不讳之朝,实愿罄其狂瞽。”太宗称善,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,必使谏官随入,预闻政事。有所开说,必虚己纳之。
贞观五年,太宗谓房玄龄等曰:“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,喜则滥赏无功,怒则滥杀无罪。是以天下丧乱,莫不由此。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,恒欲公等尽情极谏。公等亦须受人谏语,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,便即护短不纳?若不能受谏,安能谏人?”
贞观八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朕每闲居静坐,则自内省,恒恐上不称天心,下为百姓所怨。但思正人匡谏,欲令耳目外通,下无怨滞。又比见人来奏事者,多有怖慑,言语致失次第。寻常奏事,情犹如此,况欲谏诤,必当畏犯逆鳞。所以每有谏者,纵不合朕心,朕亦不以为忤。若即嗔责,深恐人怀战惧,岂肯更言!”
贞观十六年,太宗谓房玄龄等曰:“自知者明,信为难矣。如属文之士,伎巧之徒,皆自谓己长,他人不及。若名工文匠,商略诋诃,芜词拙迹,于是乃见。由是言之,人君须得匡谏之臣,举其愆过。一日万机,一人听断,虽复忧劳,安能尽善?常念魏徵随事谏正,多中朕失,如明镜鉴形,美恶必见。”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。
贞观十七年,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:“昔舜造漆器,禹雕其俎,当时谏者十有余人。食器之间,何须苦谏?”遂良对曰:“雕琢害农事,纂组伤女工。首创奢淫,危亡之渐。漆器不已,必金为之;金器不已,必玉为之。所以诤臣必谏其渐,及其满盈,无所复谏。”太宗曰:“卿言是矣。朕所为事,若有不当。或在其渐,或已将终,皆宜进谏。比见前史,或有人臣谏事,遂答云‘业已为之’,或道‘业已许之’,竟不为停改。此则危亡之祸,可反手而待也。”
评花担,折柳杯,诗酒醉淋漓。觅句鸾笺重,笼灯翠袖随。别院漏声迟,扶
醉人销金帐里。 春情
香随梦,肌褪雪,锦字记离别。春去情难再,更长愁易结。花外月儿斜,淹
粉泪微微睡些。 京城访友
桃凝露,杏倚云,花院望星辰。尘土东华梦,簪缨上苑春。趿履谒侯门,吟
眼乱难寻故人。
摩空赋,醉月觞,无地不疏狂。貂帽簪花重,鸳帏倚玉香。清楚绿鬟妆,扶
我入温柔醉乡。
咏春蚕,疑夏雁,泣秋蛩。几见珠围翠绕,含笑坐东风。闻道十分消瘦,为我两番磨折,辛苦念梁鸿。谁知千里夜,各对一灯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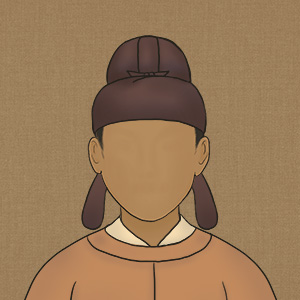 吴兢
吴兢 白居易
白居易 吴西逸
吴西逸 乔吉
乔吉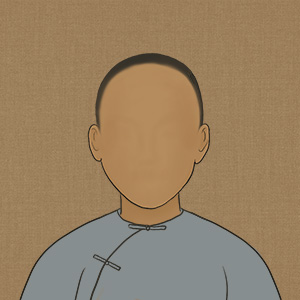 王国维
王国维 蒋士铨
蒋士铨 蒋捷
蒋捷 牛希济
牛希济 毛泽东
毛泽东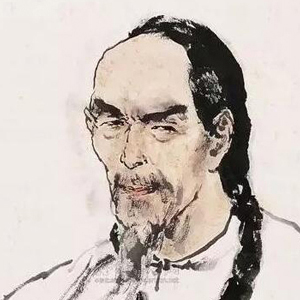 龚自珍
龚自珍 周邦彦
周邦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