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岳,南宋诗人。生卒年不详,字子西,贵池(今属安徽)人。因读书于贵池齐山翠微亭,自号翠微,武学生。开禧元年(1205)因上书请诛韩侂胄、苏师旦,下建宁(今福建建瓯)狱。韩侂胄诛,放还。嘉定十年(1217),登武科第一,为殿前司官属。密谋除去丞相史弥远,下临安狱,杖死东市。其诗豪纵,有《翠微北征录》。
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,无从致书以观,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录毕,走送之,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,余因得遍观群书。既加冠,益慕圣贤之道 ,又患无硕师、名人与游,尝趋百里外,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。先达德隆望尊,门人弟子填其室,未尝稍降辞色。余立侍左右,援疑质理,俯身倾耳以请;或遇其叱咄,色愈恭,礼愈至,不敢出一言以复;俟其欣悦,则又请焉。故余虽愚,卒获有所闻。
当余之从师也,负箧曳屣,行深山巨谷中,穷冬烈风,大雪深数尺,足肤皲裂而不知。至舍,四支僵劲不能动,媵人持汤沃灌,以衾拥覆,久而乃和。寓逆旅,主人日再食,无鲜肥滋味之享。同舍生皆被绮绣,戴朱缨宝饰之帽,腰白玉之环,左佩刀,右备容臭,烨然若神人;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,略无慕艳意。以中有足乐者,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盖余之勤且艰若此。
今虽耄老,未有所成,犹幸预君子之列,而承天子之宠光,缀公卿之后,日侍坐备顾问,四海亦谬称其氏名,况才之过于余者乎?
今诸生学于太学,县官日有廪稍之供,父母岁有裘葛之遗,无冻馁之患矣;坐大厦之下而诵《诗》《书》,无奔走之劳矣;有司业、博士为之师,未有问而不告,求而不得者也;凡所宜有之书,皆集于此,不必若余之手录,假诸人而后见也。其业有不精,德有不成者,非天质之卑,则心不若余之专耳,岂他人之过哉!
东阳马生君则,在太学已二年,流辈甚称其贤。余朝京师,生以乡人子谒余,撰长书以为贽,辞甚畅达,与之论辩,言和而色夷。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,是可谓善学者矣!其将归见其亲也,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。谓余勉乡人以学者,余之志也;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,岂知余者哉!
古之传者有言: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,曰: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:“戏也。”周公曰: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。
吾意不然。王之弟当封邪,周公宜以时言于王,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。不当封邪,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,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,其得为圣乎?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,必从而成之邪?设有不幸,王以桐叶戏妇寺,亦将举而从之乎?凡王者之德,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,虽十易之不为病;要于其当,不可使易也,而况以其戏乎!若戏而必行之,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
吾意周公辅成王,宜以道,从容优乐,要归之大中而已,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。又不当束缚之,驰骤之,使若牛马然,急则败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,况号为君臣者邪!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,非周公所宜用,故不可信。
或曰:封唐叔,史佚成之。
岁惟丁卯,律中无射。天寒夜长,风气萧索,鸿雁于征,草木黄落。陶子将辞逆旅之馆,永归于本宅。故人凄其相悲,同祖行于今夕。羞以嘉蔬,荐以清酌。候颜已冥,聆音愈漠。呜呼哀哉!
茫茫大块,悠悠高旻,是生万物,余得为人。自余为人,逢运之贫,箪瓢屡罄,絺绤冬陈。含欢谷汲,行歌负薪,翳翳柴门,事我宵晨,春秋代谢,有务中园,载耘载籽,乃育乃繁。欣以素牍,和以七弦。冬曝其日,夏濯其泉。勤靡余劳,心有常闲。乐天委分,以至百年。
惟此百年,夫人爱之,惧彼无成,愒日惜时。存为世珍,殁亦见思。嗟我独迈,曾是异兹。宠非己荣,涅岂吾缁?捽兀穷庐,酣饮赋诗。识运知命,畴能罔眷。余今斯化,可以无恨。寿涉百龄,身慕肥遁,从老得终,奚所复恋!
寒暑愈迈,亡既异存,外姻晨来,良友宵奔,葬之中野,以安其魂。窅窅我行,萧萧墓门,奢耻宋臣,俭笑王孙,廓兮已灭,慨焉已遐,不封不树,日月遂过。匪贵前誉,孰重后歌?人生实难,死如之何?鸣呼哀哉!
也莫向竹边孤负雪。也莫向柳边孤负月。闲过了,总成痴。种花事业无人问,惜花情绪只天知。笑山中:云出早,鸟归迟。
 华岳
华岳 宋濂
宋濂 柳宗元
柳宗元 陶渊明
陶渊明 关汉卿
关汉卿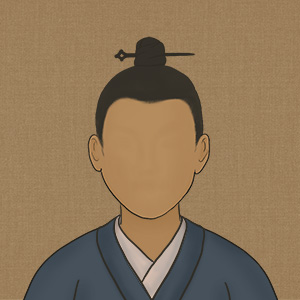 曾瑞
曾瑞 韦庄
韦庄 韩偓
韩偓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辛弃疾
辛弃疾